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。
【自由副刊】童偉格/河岸與最後一人
 圖◎阿普航空
圖◎阿普航空
◎童偉格 圖◎阿普航空
如果有一部無法由人寫出的理想小說,是以「人的重生」做為主題,那麼《罪與罰》便是它的序言。因在《罪與罰》尾聲,杜思妥也夫斯基帶我們確認了拉斯柯爾尼科夫和索尼雅之間,終於發生的雙向認肯:躺在流放地的牢房裡,當他下定決心,在未來,要以「無限深摯的愛情」,「來補償她所受的一切痛苦」伊時,在左近某處,她亦「幾乎為自己的幸福而驚慌不安」。杜氏說,一個關於「人逐漸再生」的故事才正要展開,但《罪與罰》自身,則「到此結束了」。令小說讀者好奇的,自然不是在上述彷彿人間的最後一個黑夜裡,由杜氏圈點出的,穿越重重牆垣的簡明光照;而是隨著這最後光照,彷彿,拉斯柯爾尼科夫才首次「看見」了索尼雅的實然在場――這是一個事關認識論的問題:似乎,對他而言,在那之前,她毋寧從來就更像是某種後設話語,相對概念;或者,是某種將無盡苦難,全收束在一個針尖上的擬像。
以星體對星體的尺度
最初,她是父親馬爾美拉陀夫懺悔錄裡的一個主題,代表父親無法平視的聖潔。之後,她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認知裡,是妹妹杜尼雅的延異;而其實,正是她比杜尼雅更無辜、無所求,卻仍難逃受苦此事本身,使他察覺了索尼雅,那也許更其「尊貴」的犧牲。索尼雅:另一位更本質性的杜尼雅。於是,當《罪與罰》篇幅甫過半,機器神降臨――因意外獲得一筆遺產,母親與妹妹得以在彼得堡自立,且也開始擘畫未來――那刻,負罪者拉斯柯爾尼科夫旁聽,立即明白,自己應當遠避這種關於共同生活的想像,以免破壞她們的幸福。他且也就不再延宕,離開她們,逕直走向那另一位杜尼雅,去向她道別。
那是裁縫某的住所,位在河岸上。裁縫一家九口,或病或殘,或癡愚,將家屋切割出一角奇形怪狀的空曠,具體說來,「像一個棚子」;且格外不帶批評地,容讓索尼雅寄居其中;且在可見未來裡,亦將繼續這般身無長物地寄居。於是,跟索尼雅道別,就像是跟世間最底密室裡的最後親人道別,而在別過之後,拉斯柯爾尼科夫即像能褪盡人的話語和情感,交予這位最忠誠的值勤者寄存;從而,也就能獨自跨過門檻,行進那不乏魍魎魑魅的流放地。兩人間最初的對話,是拉斯柯爾尼科夫跟索尼雅確認時間。索尼雅回答,她聽見房東的鐘剛剛打過,是晚間十一點了――隔牆,時間亦只像是有人,悄悄容讓她去租借的聽聞;而這一準確借閱,彷彿將是夜恆久指定,令其不再流逝。不妨想像:杜氏所欲在小說尾聲描繪的,「人間最後一夜」裡的雙向認肯,已預先由此漫漶開來,只因說來怪異也自然:經過半部小說,在此「對時」一刻,兩位小說主角才終於獨處。
認真想來,之前,在眾人環伺時,他們其實也只見過彼此兩面。似乎,我們僅能想像某種巨視,方能明白在那零餘幾次照面裡,拉斯柯爾尼科夫對索尼雅的識讀。例如以星體對星體的尺度。或者,像是從太陽的視域,去探看某人如夸父,想像後者那般漫長直至力竭的奔波,在前者看來,可能,形同從來就不曾真正移動過步伐;但其實,是無數次的路徑轉換,皆已在取消時序意義的情況下,被迫視成一幅細節繁疊的全景圖了――對前者而言,後者同步且全然地,據在於任何後者曾據在過的地點。
心之變異的深刻恐懼
一如是夜,拉斯柯爾尼科夫靜坐在一張破椅上,看室內燭光搖曳,泛黑的壁紙蜷曲,猜想她,在之前與此後的每一個工作日,或者,形同在不斷重複的同一天裡,如何在這陌異屋內,一再變過自己臉容衣裝,去站到大街上盡職謀生。一如初次見面時,在她父親臨終前刻,她從大街上被喚回家,出現在那間絕望而悲涼的死屋裡。當時一室,亦是這般燭照光影。他看她那條鐘式裙襬,很突兀地堵住房門,猜想可能如何,她煞費一番苦心,才買到這樣一身雖然一眼可辨、必定是極其廉價的花緞衣服。最使他悲傷的,是她手上的一把法式小陽傘,只因「雖然夜裡用不著帶,但她還是帶了」。
在她瘦小身軀之外的,一切生疏的多餘,或荒謬的費心,即連是插在那頂圓草帽上的一根鮮豔羽飾,對拉斯柯爾尼科夫而言,皆像拖曳且蟻行著她所經過的,那一整片老早就無動於衷了,而她卻曾以自己寥寥的人生經驗去盡力揣摩,且要求自己一再去取悅的街區。於是看著她,竟也像是獨見一切自異於她的,如何仍在持續環繞她――一種我們熟悉的杜氏跳躍:瞬間,拉斯柯爾尼科夫彷彿理解,索尼雅某種恆定卻纖細的不可見,如何受圍在一切顯而易見的表象之內。索尼雅在場形同不在:對拉斯柯爾尼科夫而言,她具體是人世的空缺。
於是,在他的視域裡,兩人這首次獨處,因其從先前相似死屋中所抽繹的、與所差異擺置的細節重複――如燭光,如桌椅櫥櫃,如低抑的窗,凡此種種――具象地,為他常習了兩人在正常人世裡的最後獨處。這且也是空間的恆定:對拉斯柯爾尼科夫而言,索尼雅能租得的任何房間,都像是同一個房間;都形同世上,最後猶然寬許人倖存的庇護所。
然而,在這類如守靈的氛圍裡,杜氏進一步讓我們理解:除卻上述個人心證外,事實上,他是絕對無法理解她的。在終於意識到、且提防起索尼雅那對他而言,極具「傳染性」的宗教情感後,「也許,」他挑釁地說,「上帝根本就不存在」。他想為她抹消,或為自己複現的,正是她所純粹信靠的價值體系:在他看來,其上,是永遠沉默、永不回應的虛無,某種極致的空缺;其下,則是自問自答的眾生,種種自行其是的翻譯者。其中,有代行天譴之人,有無由自咎的受難者;當然,也總不乏因自苦與自咎,而自覺聖潔過人的偽「約伯」們。
他想質疑她,或反問自己的,是自己對人世間,種種心之變異的深刻恐懼與憐憫。因為這樣矛盾的情感,他膜拜她那「偉大的受苦精神」;但隨即,他又痛切地逼問無由地受苦,或那般平靜地接受苦難,究竟有何意義。
小說家的劇場造景術
索尼雅自然無可應答,只因關於索尼雅,奇特的是:她將自己的信仰,視作一個「祕密」,向來羞於向人表述。這種情感的起始無從追溯,似乎,早在她被殘酷人世給徵用,甚至,早在她能理解話語之前,就已蘊藏在她心底。
更奇特的是,在她如向來那般,失語於自己對一切的誠摯時,那位漫長埋伏了半部小說、僅供默念的亡靈,自這守靈氛圍裡起身,代她去應答――因為櫃上一本破舊的《新約全書》,索尼雅提及贈書的亡友之名;上星期,她且去參加了亡友的追薦會。亡友正是麗紮韋塔。此刻,這處疊架小說中一切死屋的房間四壁,只祕密對那謀殺現場的唯一逃生者,拉斯柯爾尼科夫兌實。
關於那個謀殺現場,他記得開初,亦是隔牆,他如聆聽喪鐘敲響般,仔細諦聽一陣細瑣的腳步聲,接著是一陣輕微的呼喊聲;接著,「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」了。他等候任何可能的變化。直到感覺這一回,這片寂靜彷彿將是永恆伊時,他攜起斧頭,直奔而出。在那個阿廖娜死臥的房間裡,他看見死者的妹妹麗紮韋塔,不知何故,竟提前返家了的麗紮韋塔,因驚嚇過度,僅能木然望著死者,再動彈不得,也再發不出喊。他舉斧,逼近這片永恆的創造者。
一位狩獵管理員,曾如此描述遭獅群圍攻的狒狒,在臨死前刻的最後反應:在自知大難難逃之時,牠伸手遮住雙眼;這是牠最後的抵禦,彷彿牠寄望著,倘若自己不觀看,眼前的暴亂,也就將被衝散成更暴亂的量子態――可能,獅群將不是獅群;死亡也就不會是死亡。然而,眼前,無辜的麗紮韋塔,已然退化到連狒狒都不如了,直到斧頭落下一刻,她「連手也沒有舉起來遮臉」。
麗紮韋塔的全然絕望,與全無反抗,像是一種更直接的反問或對視,關於也許無人,有辦法為拉斯柯爾尼科夫解答的基本事實:人能否藉由無辜受苦,去救贖他者。當然,此刻,索尼雅並不明瞭拉斯柯爾尼科夫心中曾湧現、與一併攜行的風暴,但似乎,正是這樣一種在兩人之間,重新確立的特異距離,使得當他離去時,她就「像望著一個瘋子一樣望著他」。或者,那像是觀望一艘遠去愚人船上的乘客,揣想著從他的認知,時空規則的從此相互逆反:對他而言,時間永遠固著在受苦一刻;而空間,卻持續隨他的漂流,在舷窗外奔逃。
在索尼雅的定視裡,拉斯柯爾尼科夫原地流放。不妨想像:屋外,那條始終不被描述的河,將暗湧過小說後半部,直至尾聲,兩人更其漫長的重逢,或真正的相遇之景。這是杜氏的劇場造景術:其實,只要我們將擁擠的彼得堡,變易成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大草原;只要倒轉夜以為日,照亮這個場景,我們就會看見在那另一處「河岸」上,另一處「棚子」裡的,那另一位拉斯柯爾尼科夫,置身於《罪與罰》的最後一個白日裡。彷彿,拉斯柯爾尼科夫從來就不曾邁開過腳步,而其實是索尼雅,如此負罪地跋涉過無數被他遺棄的地景與時程,逕直走向那猶然寬許他的同一庇護所。
話語繁複的《罪與罰》如此,是《罪與罰》自身話語的簡潔反喻:在這個相對的觀看尺度裡,雙向的認肯,在可以輕易逆反的表象細節底重新締結,或其實從未解散締結。一如拉斯柯爾尼科夫曾經對她的複視,在索尼雅的視域裡,終究,舊日世界重新歸結了拉斯柯爾尼科夫,成為世上最後一人。
那必然使她感到生疏,或「驚慌不安」,一如其實,善良如她,從來就不曾深悉他,但這卻從來無礙她的惜愛。而杜氏,為我們重新埋藏這個「真正的祕密」,歸結整部小說,成為無可寫就之理想小說的序言。●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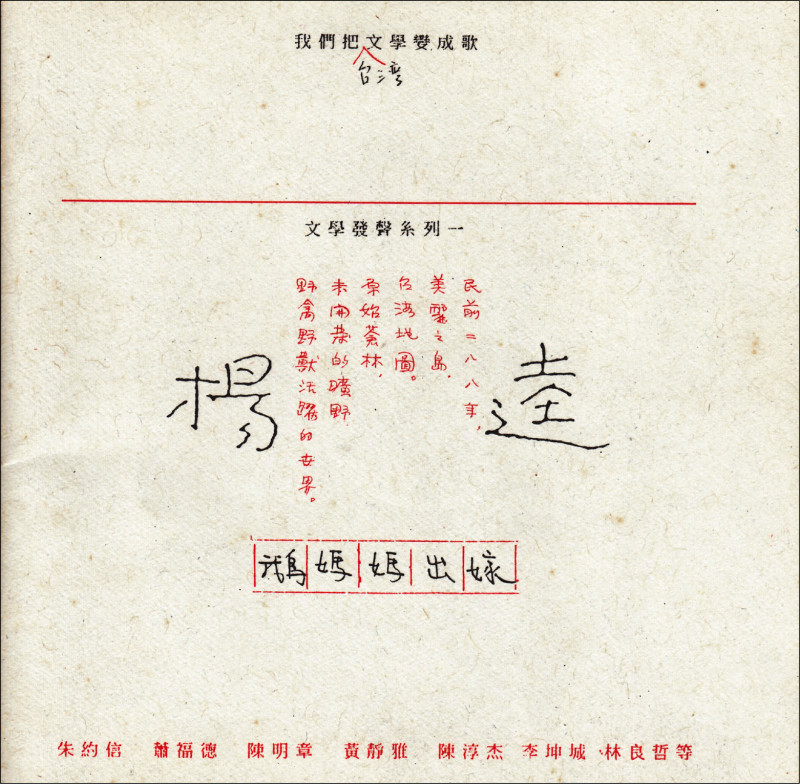



網友回應